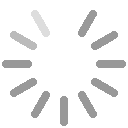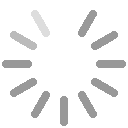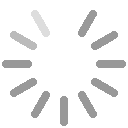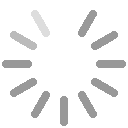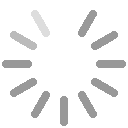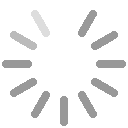粗暴麻木的父母,病危垂死的老人,粗野疯狂的“洛丽塔”,在大漠中谱写着一支属于克里雅人的狂想曲。
第五天了,随着商队,骑着骆驼穿过戈壁,爬过无数沙丘后,我终于到克里雅河畔的达里雅博依乡以南的这个牧业点了。整整五天我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跟着驼队在骄阳下赶路,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睡了还是清醒着。我不在意,我知道,这头总想吃我头发的骆驼会把我带到那片沙漠中的绿洲。
这支驼队是我在于田县城遇见的,他们是一些准备去达里雅博依乡,用面粉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换取克里雅人羊皮的商贩。遇见他们后我改变了准备租越野车去的想法。
摊开地图,33.76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内,惟有大河沿(达里雅布依的汉语名)孤零零的标注着。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克里雅河畔的达里雅博依乡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263户、1290位克里雅人分散居住在克里雅河下游的110多万亩胡杨、红柳丛林里。克里雅人说维※※语,信仰※※※教,不识耕种,以牧羊为生。克里雅河,维※※语,飘移不定的河流,两岸直至沙漠腹地。
一路上我的向导居马,这个二十五岁,在沙漠中穿着西装的维※※族青年总是不停的询问我为什么要去达里雅博依以南的那个牧业点。年轻的居马总是喜欢有意无意的漏出别在腰间的那个老式的手机,虽然在这沙漠中根本就没有手机信号。我说我去旅游,居马不解的问为什么来这里旅游,他说这里除了沙漠还是沙漠,一无所有。
初到达里雅博依乡以南的这个牧业点的那天起风了,漫天的黄沙吹得我睁不开眼。朦胧中我看到了几座在克里雅河畔与胡杨林之间用红柳搭成的小木屋,这就是达里雅博依乡以南的这个牧业点的全部。克里雅人居住的房子是用胡杨、红柳排扎而成,墙体涂抹草泥,房顶铺以较厚的芦苇,房门是由一棵粗大的胡杨木刳空而成。由于风沙的侵蚀,大多数的房屋墙泥都已脱落。放眼望去,这里的绿洲与荒漠相比是那么的可怜,而又那么的让人珍惜心痛。
傍晚,居马把我安排在了一名叫阿尔斯郎的村民家,他临走时说这里什么都不好,只有克里雅人的心是好的。三十五岁的阿尔斯郎上前用他粗糙的大手握住了我因水土不服已开始脱皮的双手。我把一些砖茶与冰糖送上后,阿尔斯郎显的很是有面子。三十五岁的阿合买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主妇帕丽旦的丈夫,是这片绿洲的国王,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坐在小屋中的火塘旁相互问候时我发现有一只幼嫩的,充满敌意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目光的主人是古丽(汉译:花朵),阿尔斯郎的女儿。
生活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原帖链接:
#p#
当我问阿尔斯郎在这里生活多久时,他木然的望着我,似乎并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我再次重复了自己的问题时他才说不太清楚,他说他父母都是克里雅人,他爷爷也是克里雅人,再往上他就不知道了。克里雅人的历史世代口传,不用文字记载,年长的老人就是他们的历史。关于沙漠深处克里雅人的来历,一种说法是克里雅人为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后裔,为逃避战乱翻越昆仑山进入了这片绿洲;另一说法是克里雅人原来就是这里的沙漠土著民族;第三种说法最有传奇色彩,即克里雅人是2000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楼兰人的一支。而阿尔斯郎并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克里雅河。他说他们克里雅人就是追随着克里雅河生活的,有河水的地方才有牧草,那些牧草养育着他们的羊群也养育着他们的子女。克里雅人没有定居的概念,河水流到哪儿他们就迁移到哪儿,胡杨林生长到哪儿他们就住到哪儿。克里雅河水的多少决定着牧民们在一片土地上停留的长短,而克里雅河的断流与改道从未给过克里雅人任何准备。
阿尔斯郎一天的工作基本上只有砍柴与维护那口水井,克里雅河昏黄的河水是无法直接饮用的。他的妻子帕丽旦负责一些家务事与一日三餐及羊群的照料。两个孩子则每天跟随着羊群在克里雅河畔游荡。阿尔斯郎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背靠着他那座红柳搭成的小屋,抽着土烟木然的望着远方,谁也不知道他在守望着什么。他与这片沙漠保持着同样的沉默,面对我唐突的采访时才会不知所措的回答几句。
只有黄昏时,古丽带着羊群与他的弟弟回来时家中才多了一份热闹与温情。小屋内的火塘的火光映红每一个人的脸庞,安静的夜如河水般流过这片沙漠的上空。古丽总是喜欢翻弄我的摄影包,她把里面能拉出来的东西全部拉出来,撒的满地都是,而她的弟弟则害羞的躲在母亲身后。古丽野蛮的抓着我,命令我教她玩这些照相机及摄像机。当她看到自己出现在摄像机的小屏幕上时大声尖叫一声,那尖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古丽睡了,我一个人收拾散落满地的摄像器材。
生命与渴望的歌声
原帖链接:
#p#
孤独的等待
几日的走访中我了解到 这个牧业点有十一户人家,当然都是以放羊为生,过着一样的生活。克里雅人并没有自己辉煌的文化,也没有在历史中展露头角,他们只是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他们那片孤独的圣地。他们所拥有的是和这个沙漠一样的性格,和他们精神永不停息的源泉《※※※》。我每到一户人家时所面对的都是那些惊恐的面孔,在我说明来意后所看到的又是一种略带诚恐而又惊喜的面容。在那些被风沙吹得粗糙的面孔上你是很容易理解他们的笑容为什么是那么的夸张而又干涩。一杯苦茶,一支能让你喉咙冒烟的莫合烟就是一次来访的开始。闲聊中我望着他们热切的眼神,却不知他们在渴望什么。
最早将克里雅记载于文字的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另一个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借着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探险家、考古学家的不朽著作,克里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被世人所知晓。然而,几十年过去后,他们现在的生活却比以前更艰难了。牧民们只是说克里雅河的水越来越少了,他们对此根本无法理解。克里雅河,这条发源于昆仑山脉的乌斯腾格山,经于田县向北流进塔克拉玛干沙漠二百多公里的河流,在年均降水量14毫米,蒸发量3000毫米的环境中挣扎着。而现在这条克里雅人的母亲河已在整体环境恶化的大环境中病倒了。随着牧草的减少,羊群也不得不减少了。现在,即使是每年雨季水量最大时,克里雅河也只是流进沙漠100来公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里已成为了浩瀚沙海中的孤岛。关于环境问题克里雅人是无法理解的,但他们依然要承受这种莫名的苦难。阿尔斯郎说曾经有过牧羊人带着羊群来到这里,想与他们一起生活。他们款待了牧羊人后让牧羊人离开了克里雅河。阿尔斯郎说这片※※赐予的土地已无法养活更多的人了。
原帖链接:
#p#
这里的生活方式是极其单调的,没有水电,没有道路,整个世界中只有漫天的黄沙,傲然挺立的胡杨,和那静静流淌的克里雅河。苦涩的风尘,苦涩的生活,是那种古老的传统与生活方式维护他们脆弱生活的支柱。这个牧业点只有十一户人家,每户人家还都有些距离,并不是集中在一起的。有时我在想,他们难道不会感到孤独吗?老人库尔班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孩子在于田县城找到了工作,想接他进城养老,于是两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出生地去往县城。到了街上一下车,他逢人就躬身握手,表示问候,结果发现人太多了,怎么也没有办法向每个人都表示自己的问候与祝福。库尔班还以为外面的世界也如同达里雅布依一样,人人皆是兄弟。不到一个月,他就偷偷跑回来了。他说,县城的人没有礼貌,见到长者不问候。还有,城市太吵。库尔班说在这里自己感觉离※※更近一些。一位老人不喜欢城市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可在这里还有着关于城市的渴望,关于逃避宿命的挣扎。
一日,我在胡杨林中进行拍摄时遇见了古丽,她正把她的弟弟骑在身下痛打,他弟弟也在还击,这已经不是打闹了,古丽在和她的弟弟打架。我上前去拉开古丽,可古丽像疯了一般尖叫着要咬我的手腕,并用一切肮脏的,下流的词汇来咒骂我。古丽的弟弟爬起身后一改往日的羞涩也开始打我。最终我放开了古丽的手,手腕上留着古丽紫黑色的牙印。我看着这对姐弟领着羊群消失在胡杨林中突然感到内心中有一种莫名的茫然。这种半游牧的生活使两个原本应该在教室中读书的孩子,本因拥有希望的孩子在这片沙漠中无法逃避自己的宿命。
金秋的幻想
帕丽旦烤了很多面饼,我不解就问她今天为何烤这么多面饼。她依然低着头忙着烤自己的面饼说一个老头,一个萨朗(汉译:傻子)要死了,这两天他没吃的了。我还不知这里还有一位傻子老人,她说他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饭后,阿尔斯郎要去给那个老头送面饼,我就和他一起去了。
在去寻找老人的路上阿尔斯郎和对我讲述了关于老人的一些故事。翟乃图以前也和所有克里雅人过着一样的生活,直到他三十岁时命运才现楼了它真实地面目。二十年前的一天,翟乃图的妻子去放羊,之后的第二天也没有找到他的妻子,只找到了那些羊群。他的妻子仿佛被那些终日的风沙带走了一般没有了任何的消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翟乃图一时无法接受。他带着他和妻子的孩子在克里雅河畔等候妻子,三年后他的妻子没有来,他的孩子却又离开了他,在他怀中一点一点的病死了。后来克里雅河改道了,连河水离开了他。翟乃图没有随着克里雅河迁徙了,他依然住在他们曾经的家中等候着自己的妻子。现在他快要死了,但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帕丽旦即给他烤饼又叫他(萨朗)傻子,就像我始终不曾理解这片沙漠一样。
翟乃图住在一个树枝搭起的窝里,我实在难以称它为房子。我和阿尔斯郎低着头将钻进了翟乃图的窝中。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在这远离人世,远离河流的荒漠中顽强的生活了二十年,他现在瘦弱的只剩下一堆骨头了。翟乃图看到我们来了,热情的起身与我们握手,我握到了一只黑瘦的,已几乎没有了肉的手。翟乃图的精神依然很好,表示过对我的欢迎后就和阿尔斯郎开起了玩笑。我望着那些从树枝见散落而下的阳光落在翟乃图已失去生气的脸庞上感到一种难以克制的悲伤。翟乃图讲几句话就要咳嗽,黑色的痰落在我的脚边。这里也没有医院,或许翟乃图已不再需要医院了。
原帖链接:
#p#
在返回的路上阿尔斯郎笑着说翟乃图是个(萨朗)傻子,和他的妻子语气一样。
回去后帕丽旦正在打古丽,用一根红柳条。古丽的左臂上已是血肉模糊,有一条很大的伤口赤裸着。帕丽旦咒骂着她的孩子。古丽为了去掏鸟窝从胡杨上摔了下来,左臂被树枝划了一个大口子。帕丽旦打古丽的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打了古丽后她才不会再次弄出这样的伤口了。古丽不敢闪躲母亲的鞭打,望着我,不去看那可怕的柳条。我喊着(抱了得)好了,把古丽藏在身后,我从背包中取出药品涂抹在古丽的伤口上,帕丽旦随手抓起一把炉灰涂到了古丽的伤口上。
那天晚上阿尔斯郎问我还要在这里停留多久,我说过几天就要走了。他说很可惜,下个月就是古丽的婚礼了。她可以嫁到雅博依乡里去了,阿尔斯郎对此感到很高兴。我问他古丽见过自己未来的丈夫吗,阿尔斯郎说没有。怎样去理解这片大漠?我不能有任何无力的指责,这里没有学校,唯一的学校在达里雅博依乡。无法上学,这里的女孩都在很小的时候就结婚了。在沙漠中一个女孩除了结婚与生育她就很难找到自己的意义。古丽倔强固执的眼神,粗野的性格都将会随着她的婚姻生活而散落在漫天的沙尘中。在沙漠中的希望和这里的生活一样艰难,所有的希望只能是多年后古丽的孩子可以在教室中而不是去牧羊。
离开的日子来临了,我最后一次去拜访翟乃图。他已经躺在地上很难起身了,木然的望着远方苍茫的荒漠,那种表情可以从每个克里雅人面容中体会到。我没有说什么,留下了一些白糖与茶离开了这里。在返回的路上挂起了大风,满天的风沙让我睁不开眼,突然一粒砂砾钻入了我的眼睛。这是那么的疼,干涩的风又是这样的割脸,眼泪不停地流。
古丽被母亲打出了门,站在离家不远的沙漠中遥望着远方,望着克里雅河的左岸。阿尔斯郎说小孩子不懂事,不愿意出嫁,要留在家里。帕丽旦说她过会儿就会回来的,她说这就是克里雅人。到了晚上古丽还没有回来,阿尔斯郎夫妇在火光中商量着古丽的婚事,我悄悄起身走向那片沙漠,走向这沙漠中唯一的,永恒的花朵。古丽坐在一座沙丘上,我走过去静静的坐在她的身边。月光将这片沙漠照耀的惨白,古丽抬起头小声问我就要走了吗。我点点头,古丽突然哭了,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沙漠上迅速的消失。我摸摸她的头说回家吧,她擦着眼泪点点头依然坐着。我起身离开,走了几步后回头望着古丽。她的影子被月光拉的很长,像一条弯曲的小河,一条不会流动的克里雅河。
春天是风,秋天是月亮……
原帖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