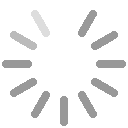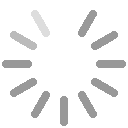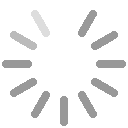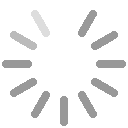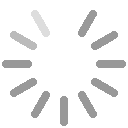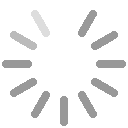西藏是不能随便去的。
理由有二:一是平均四千米以上的海拔,或轻或重的高原反应都算是旅行的累赘;二是天高云阔日光倾城,一下目睹了这般景象,日后的风景情何以堪。
所以我觉得,“旅行”这个词用在西藏身上总不够妥帖,哪有这样千辛万苦的旅行,一群人对着蓝天碧水,大口尖叫,大口喘气,大呼过瘾,大喊头痛。又可惜我们纵然行走在圣城圣湖,却总还是没有朝圣的虔诚,各自拖着疲惫的身体,满腹心事。
于是,阳光很好,蓝天很妙,我们在拉萨城下匆匆而过,不旅行,不朝拜,只目睹。


睁眼,喘气,尖叫,这世界原来也可以是这般模样
一路上都在听说※※※※的故事,无论是功勋卓著的五世,还是诗情浪漫的六世,加上亲眼所见沿途那些手持转经筒的长幼老少,那些在佛陀面前、圣城脚下五体投地的人们,还有佛像面前燃起的长明烛火,经幡上随风永动的六字真言,我十分能理解同行的一位坚强女性为何在这样的景象面前落泪。信仰,在离天最近的地方,终于还是被人们找到。在他们的世界里,焚香,诵经,跪拜,便能抚平人世里最大的哀漠与心死。而如我们一样的俗人,却从不敢轻言信仰,赌不下,输不起,只能锱铢必较地盘算生计。
在西藏,和信仰比肩的,是天空。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出我和你。

甚至,连蓝天都从来不是信徒的终点。
拉萨城并不大,布达拉、罗布林卡等景点一两日便可游完,但余下在拉萨居住的日子,却并不因此而了无生趣,要我说,只消有西藏这样的天空,整天仰脖对视便足以乐不可支个两三年。这里的天足够大,足够蓝,伸手可碰,须臾可变,拉萨城不需要动弹,便在天空之下熠熠生辉了。平生第一次见识这般盛景,似乎有降服一切的神秘力量,看惯了都市里的油烟与沙尘,此时此地,这样的高原这样的天,真是该谢天谢地。
对于很多人来说,恐怕一辈子就来那么一次西藏,头晕过,心醉过,只此一次,都豁出去了。转念一想,那些祖辈久居于此的汉人藏民,是否早已习惯这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是否在热烈的日光里甘之如饴地休养生息?到后来才发觉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就好像我们从来也不曾选择出生地一样,这里的人们一出世便被日光宠幸、被佛陀恩典,世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不需要其他人来告诉他们这里的美妙,他们心里有着更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妙不可言。这里有让人叹为观止的景致,但这里的生活并不必须惊世骇俗,纵然打开了一扇天堂的小窗,但并不妨碍这里充满着人世的小小幸福。无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对于人们的生存而言,永远都是在合适的土壤里深耕,找到最舒服的生长姿态,开枝散叶。

从宾馆的房间可以看到布达拉,于是,每夜每夜都会有人守着窗台。

佛的地界,也讲相思。
我想每一个来西藏的人都必须做一个小小的检讨,我们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刻板的预设,预设了这里的好坏,而其实在好坏之外,更多的是同与不同,千万不要因为这里太多的与众不同,而忘记了人们相同的渺小与伟大。
西藏地广人稀,但不缺生灵,每次行车赶路,跃然窗外的狗马牛羊,总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话题。无论是在去纳木错的路上遇到的野牦牛,还是在从青藏线回家的途中遇到的藏羚羊,我的镜头总是不够敏锐捕捉到它们的瞬间,而就像我这个孱弱的镜头一样,在动物们面前,人也不必清高傲慢。有谁能解它们以天为盖以地为庐的风情,有谁能懂它们低头食草仰头饮天的壮举。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荒漠里,它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如果它们也拍电影,那其中必定有最忧郁的苦情公主,最豪迈的西部英雄。我不奢望懂得它们的世界,但一路上,我都听见,牛说、马说、羚羊说:这世界是有很多样子的。
西藏这一趟,毫无疑问是我们最美的路过,我们很庸俗地欣赏这里奇异的景色,很幼稚地打探这里玄妙的奇迹和浪漫的爱情,最后终于恍然大悟,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样子的。

圣湖的子民们,在与神接近的地方栖居。

纳木错的影子,七千年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