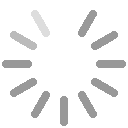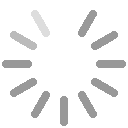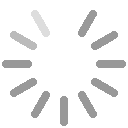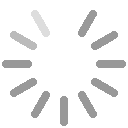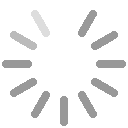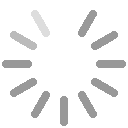极光:极光,在天文学中叫Aurora,是罗马神话中的黎明女神,是伽利略取的名字。在今天看来,极光彷佛是黎明女神挥舞着裙幔,在天空留下流光溢彩,更映衬了它充满神秘色彩的美,让无数生活在极地以外的人们无比憧憬和神往。
然而,远古的人们在充满魔幻色彩的极光面前,充满了恐惧,不管是北欧的维京人,格陵兰和北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极光在他们眼里总是和少女的亡灵,死去的冤魂,造物主的愤怒或者是战乱灾害的先兆联系在一起。夜晚,当极光在他们头上流动的时候,古人们只能躲进房内,惟恐极光从天而降,化作利刃,砍去他们的头颅。

这种对极光的无知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开始用理性的目光分析看待身边的世界。而直到近代,随着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发展,极光的神秘面纱才被逐渐揭开。极光,实际是太阳风和大气层撞击的产物。我们生活的地球,除了有大气层保护着不受小型天体直接撞击之外,还有地磁场保护着面遭宇宙射线的直接辐射。当太阳风中的等离子流以每秒300公里的速度飞向地球的时候,在大约距离地球7万公里处受到地球磁场的阻挡,并被引导到地磁两极,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这些粒子与大气层中的气体分子发生撞击。在大气层的气体分子的原子周围,分布着不同轨道的电子层,受到撞击的电子在吸收了太阳粒子的能量后从低能级轨道跃迁至高能级轨道,随后因为不稳定又重新跃迁低能级轨道,在这个回归的过程中同时释放光子,于是产生了极光。由于大气层主要包含氮气和氧气这两种成分,在受激发而发出的光线也就带有相应的特征色,类似平时通过特征光谱检测成分一样。当这个撞击发生在不同大气层高度时,也就产生了不同颜色的极光。比如绿色极光通常发生在距离地面120-180公里的高度,红色极光则在更高的高度,而蓝色和紫色极光则发生在距地面120公里以下。

虽然太阳粒子被地球磁场引导到地磁两极,但经过多年观测尤其是卫星遥感技术应用之后发现,极光发生最频繁的地带并非地磁两极上空,而是在磁极周围的一个椭圆环形地带,称为极光椭圆区(Aurora Oval),地球上90%的极光都出现在这个地带,从而也成为了观赏极光的最佳地点。但并非极光椭圆区都适合作为观赏极光的目的地,海洋,恶劣的气候都会造成种种不变,实际上,适合观赏极光也就集中在加拿大中北部,阿拉斯加北部,俄罗斯北部,北欧北部及整个的格陵兰岛和斯瓦尔巴群岛。
观赏极光,除去选择合适地点,还有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事实上,极光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可能在天空中出现,但和太阳光相比则显得如此微弱,从而超过了人眼可以辨认的范围,只有在夜空,才有可能观赏到。而极光椭圆区通常都已经进入极地范围,到了夏天,由于极昼,太阳一直悬挂在天空,所以能看到极光的季节集中在十月初到三月底。同时,由于天气,太阳活动状况等等多种因素,使得预测极光成为一件并非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有人说,观赏极光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耐心,第二个因素是耐心,第三个因素还是耐心。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那些如梦如幻的极光照片,多半是摄影师辛劳的结果。在斯瓦尔巴,晴朗的夜空意味着严寒,满天繁星也是零下20度甚至零下30度的代名词,每张极光的照片背后都有可能写满了艰难。
在斯瓦尔巴守候了数个夜晚一直无缘以见。直到离开前的倒数第二个晚上,我归还了租来的雪地摩托之后,已经快晚上7点了。从早上8点多吃过早饭之后,就骑着雪地摩托到处跑,忙着拍照,人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11个小时滴水未进。天色渐暗,同时一改白天的静谧,狂风四起,卷着地上的积雪扬起数米高,温度越来越低,但天空却依然清朗。这样的天气下出现极光应该不属意外。趁着天色还亮,我躲进海湾边一个用作雪地摩托库的帐篷里,一边听着风肆虐着帐篷的帆布发出的呼啦声,一边从羽绒衣里拿出保温壶就着能量棒和什锦干果充饥。保温壶的水是在归还摩托时要来的新鲜开水,但放在摄影包里的能量棒一直就处于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下,硬得和石头棍一般,只能塞进嘴里,用最里面的牙使劲咬断,然后喝口热水,让巧克力在口中慢慢融化。吃了几根能量棒,再抓了两把干果塞嘴里之后,重新走出帐篷,来到海湾边,让自己对摄影执着,再次接受极地风雪的考验。
这片海湾在朗伊尔宾最北,叫Adventfjorden,这段也是它的最东端,向西北延伸,通向Isfjorden海湾,向东则是大片叫 Adventdalen的旷野,向北越过狭窄的Adventfjorden是片小山头。这里是在朗伊尔宾附近最大的一片开阔地带,实际在每年太阳节之前,就已经能在这里看见太阳了。不过在这样的开阔地带上,从东边吹来的风没有任何屏障,狠狠的把能量发泄在这片海湾边。在气象学中,除了有气温这一指标外,还有另外一项成为风寒指数(Windchill)的指标,也就是气温和风速综合影响,就是人体感觉到的温度。比如,在气温是零下20度的时候,如果风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那么风寒指数就是零下33度。相比朗伊尔宾的街道上,海湾边的感觉到的温度少说还得低上5,6度。
走到海边,支好三脚架,换上超广角镜头并对准北方的山头,快门调到B门状态,拧好快门线,做好准备工作后塞上耳机就这样傻傻的站在风里,仰着头四下观望等候极光。必须承认,怀着极大的期待连续等候极光数个晚上未果,而归程渐近的时候,我眼前开始不断出现幻觉,很多时候自己无法辨别天边到底是天边云彩的反光还是极光。等了一个多小时,朗伊尔宾上空又产生一小片亮斑,我自己跟自己说,那不过又是片云,反了点地面的灯光罢了。酝酿了一两分钟后,那片亮斑忽然伸出一角,颜色开始转绿,并在我头顶上向北扩展,成为一道细长的亮光,同时北边山头后面也产生一片绿光,如同火焰一般熊熊升起,和我头顶的亮光呼应着,并不停的扭动着自己的躯体,柔若无骨。我赶紧摁下快门线按钮,并锁住旋钮。这就是极光,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上天把极光恩赐于我。我独自在风雪里高声吼着,让这种无法形容的感觉发泄出来。

在这之前,我也一直暗示着自己,能否看到极光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能看到极光的地方不少,但我在这些天里感受到的,却比极光本身特别得多。比如坐着狗拉雪橇或者骑着雪地摩托看到的除了冰雪再无它物的极地荒原。
拍摄极光那天可能是最辛苦的一天,早上9点不到出门,回来已经是晚上12点多,在外面停留了15个小时多,就喝了点热水,3,4根能量棒和一些什锦干果。拍摄极光的时候极冷,所有的液晶几乎全部失灵,摁下操作键一般得等上好几秒才有反应,还显示不全。而且风大。在装备准备上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防风雪镜(goggle)和羽绒手套。在风雪里眼睛根本睁不开,带的雪镜是高山雪镜,消除96%的可见光,晚上戴了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一直是强忍着看天上有没有极光。手套就带了lafuma的windstopper抓绒和mammut的gore-tex手套,保暖性不足。在风雪里站了4个小时后,手基本都僵了,只能靠双手不断互相拍打防止冻伤。保暖内衣+长毛抓绒+重型软壳+登山羽绒,还顶不住风往身子里钻。背向风弯腰,风马上沿着下摆吹进去,浑身就一哆嗦。相机包合上,只是没拉拉练,里面就全是雪。